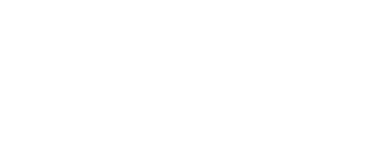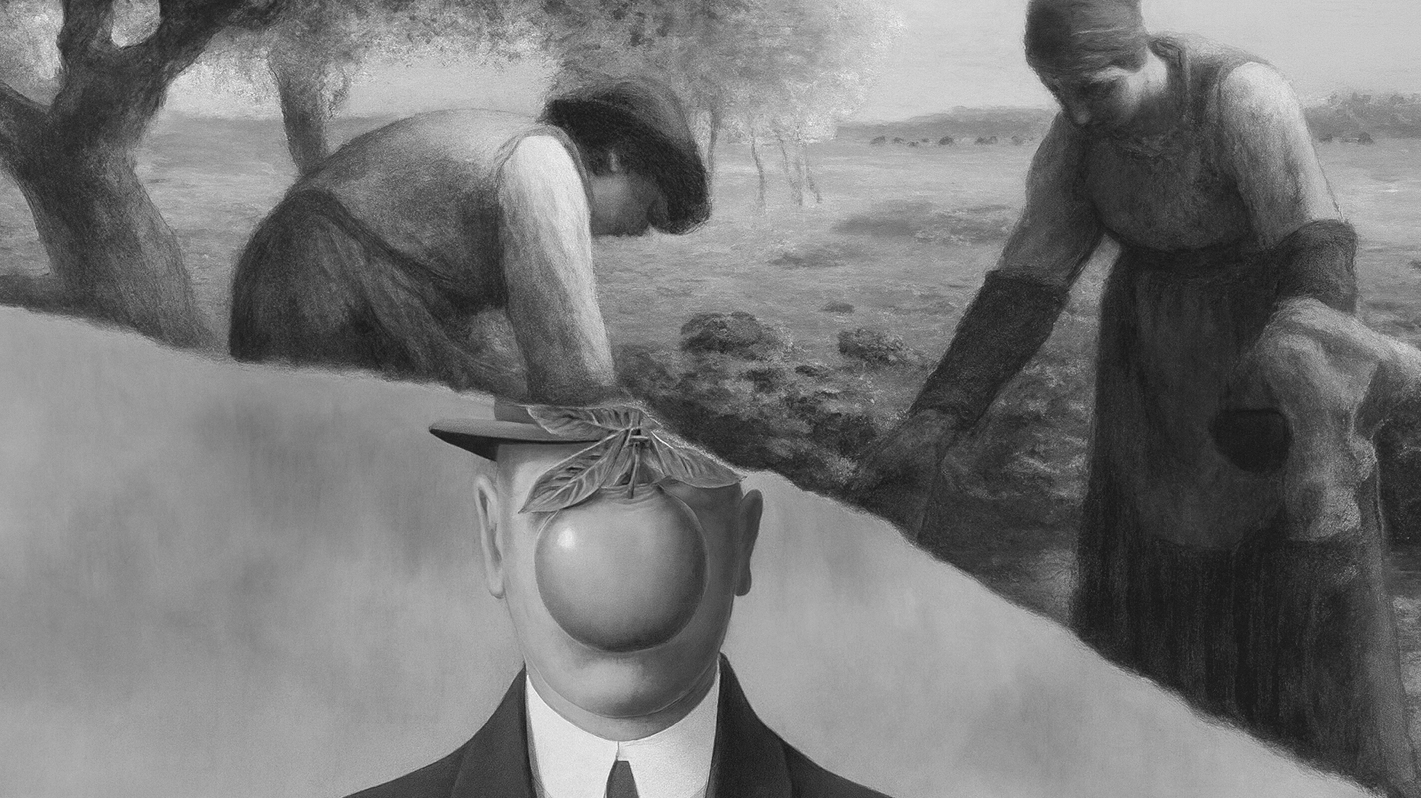當我們談論藝術史時,常常會提到一些熟悉的名字——畢卡索、米開朗基羅、梵谷。幾個世紀以來,男性藝術家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關注與能見度。
然而,在這些家喻戶曉的名字之外,還有許多女性藝術家,她們以同樣的熱情與遠見從事繪畫、雕塑與創作。儘管在當時經常被忽視,她們的作品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我們觀看與理解藝術的方式。
在這篇文章中,我們將深入認識六位開創性的女性藝術家。她們在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,每一位都發展出獨特的藝術語言,挑戰既有框架,並拓展了藝術的可能性。
艾格尼絲·馬丁 Agnes Martin|極簡藝術中的靜謐力量
我們從畫家艾格尼絲·馬丁(Agnes Martin)開始說起。她的作品乍看之下極簡又靜謐,但在表面之下,擁有著深層的情感張力。
雖然經常被歸類為極簡主義藝術家,馬丁更傾向於將自己的作品定義為抽象且具有靈性。她不追求工業化的材料或僵化的系統,而是以直覺、情感和個人經驗為創作核心。她的線條皆手繪而成,細緻而刻意保留不完美之感;她不依循固定公式選色,而是依據感受選擇色彩。在她的網格畫中,柔和的鉛筆線與低飽和的色調,構成一種沉靜而有節奏的畫面。
1950 年代初,馬丁在參加吉杜·克里希那穆提(Jiddu Krishnamurti)與鈴木大拙(D.T. Suzuki)的演講後,開始對東方哲學產生濃厚興趣。這些思想,加上她對抽象表現主義的關注,影響了她一段創作時期。這段時期的作品多半以有機形狀與溫柔的色彩呈現,如米色、灰綠、淺灰與乳白,傳達出內在的寧靜與溫暖。
馬丁經常形容自己的創作是一種「寧靜的表達」。透過細膩的線條與重複,她試圖喚起如純真、喜悅與美感等情緒狀態。她相信,真正的藝術並非來自理性思考,而是來自對美與幸福的感知。
她的畫作展現出結構、空間與靜止之間的微妙平衡,邀請觀者放慢腳步,仔細觀看,與那表面之下的世界產生更深層的連結。
露絲·阿薩瓦 Ruth Asawa|將日常材料化為藝術
露絲·阿薩瓦(Ruth Asawa)是一位美國藝術家,以精緻複雜的金屬線雕塑聞名。她的作品如同懸浮於空中的線條素描,既纖細又富有建築感,兼具輕盈與結構之美。
她於 1926 年出生於加州,父母皆為日本移民。二戰期間,阿薩瓦與家人被強制遷入日裔拘留營。儘管環境艱困,她依然持續畫畫、學習藝術,甚至向營中的其他被拘留者學習。她後來曾表示,自己沒有怨恨,並相信即使身處逆境,也能孕育出希望與力量。
雖然她最為人熟知的是雕塑作品,但她視素描為創作的基礎。她說素描是她最大的喜悅與挑戰,每天都專注於線條、形狀與節奏的練習。
1947 年,她前往墨西哥旅行,觀察當地工匠用金屬線編織籃子,這成為她創作轉折的重要靈感。她將這種工藝轉化為自己的藝術語言,創作出一系列盤旋、懸掛於空中的立體結構。隨著光線穿透作品,影子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,與雕塑本體共同構成一場空間對話。
對阿薩瓦而言,創作的過程與成果同等重要。她相信耐心與重複的價值,也相信簡單的材料有機會蛻變為非凡的藝術。
在人生後期,她成為藝術教育的積極推動者,致力於建立公共藝術計畫,讓創意教育變得更普及、可近。
對阿薩瓦來說,藝術與生活密不可分,是一種觀察、感受與關懷地形塑世界的方式。她曾說過:「藝術是一種行動。藝術與生活密不可分。」
草間彌生|從圓點走向無限
你或許曾看過她的巨大南瓜、閃爍圓點,或是無限鏡屋——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那就是草間彌生的作品。她的藝術初看之下充滿童趣與超現實感,然而在那充滿活力的色彩背後,潛藏著對創傷、執念與透過創作生存的歷程。
草間彌生於 1929 年出生於日本,從小便開始畫畫,透過藝術來整理自己的情緒與反覆出現的幻覺。她經常看見密集的圓點與圖案覆蓋在各個地方,從牆面、身體,甚至天空。她曾形容這種經驗彷彿自己正在「融進了宇宙」。這些視覺幻象雖然令她害怕,卻成為她一生藝術語言的起點。
1950 年代,她移居紐約,並逐步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,涵蓋繪畫、軟雕塑、裝置藝術與公共表演。她的創作大膽、沉浸式,經常領先時代,包括越戰期間的反戰行動與裸體彩繪抗議。然而,儘管她具有高度原創性,她的作品與觀念當時常被忽視,甚至遭男性藝術家挪用。
對草間彌生而言,重複不只是創作手法,更是一種自我療癒。她曾說:「如果不是因為藝術,我早就自殺了。」
如今廣為人知的無限鏡屋(Infinity Mirror Rooms),實際上早在數十年前便已誕生。這些沉浸式空間彷彿一場無盡的夢,觀者置身於反射與光影交錯之中,彷彿在無限的重複與閃爍中,逐漸與自我融為一體。
多年被忽視之後,草間彌生終於在晚年獲得全球關注。今天,她被譽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在世藝術家之一,並成為日本當代藝術的象徵人物。
希爾瑪·阿芙·克林特 Hilma af Klint|被遺忘的抽象先驅
當我們談到抽象藝術時,往往會想到康丁斯基、蒙德里安或畢卡索等名字。但在這些人之前,來自瑞典的藝術家希爾瑪·阿芙·克林特(Hilma af Klint)早已開始創作純粹的抽象作品。遺憾的是,她的名字卻長期被藝術史所忽略。
希爾瑪於 1862 年出生,她的作品充滿大膽的幾何結構、旋轉的色彩與象徵性圖像,風格更貼近 21 世紀而非她所處的 19 世紀。她深受神智學(Theosophy)與後來的人智學(Anthroposophy)等精神性信仰影響,並經常形容自己的創作是由「高靈」引導。對她而言,繪畫不是自我表達,而是一種通靈性的實踐——將不可見的事物轉化為視覺形式。
1906 年至 1915 年間,她創作了一系列名為《為神殿而畫》(The Paintings for the Temple)的作品,充滿抽象幾何與寧靜對稱之美。她認為世界尚未準備好理解這些作品,因此要求在自己去世至少 20 年後才可公開展出。
這些畫作直到 1980 年代才逐漸被世人看見。直到近幾十年,她才真正被認可為抽象藝術的先驅。如今,希爾瑪·阿芙·克林特(Hilma af Klint)被重新評價為現代藝術史上重要的女性藝術家之一,她將藝術帶入精神層面的貢獻,也持續在藝術界與觀者之間產生共鳴。
篠田桃紅|當水墨遇上抽象藝術
她的畫作給人一種既溫柔、簡約卻又大膽的感受,介於語言與沉默之間。篠田桃紅不只是用水墨創作——她重新定義了水墨的可能性。
篠田桃紅於 1913 年出生於中國,在日本長大,從小接受傳統書法訓練。然而,她並未走入既定的古典道路,而是將字義抽離,讓筆勢、質地與空間成為畫面的主角。
1950 年代,她曾在紐約生活多年,並接觸到抽象表現主義。她並未直接採用那種充滿爆發力的表現手法,而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視覺語言——在奔放的筆勢與寂靜的留白之間,建立起一種內斂而強烈的對話。篠田桃紅的作品常使用黑色與銀灰色調,作品看似簡約,卻充滿情感。
她的畫作不只是視覺表現,更像是一場冥想,圍繞著平衡、無常,以及動與靜之間的張力。篠田桃紅的創作體現了日本美學的核心精神,特別是「間」——對空間與時間的感知,以及「侘寂」——在克制與不完美中發現的美。
她的藝術之路並非一帆風順。27 歲舉辦的第一次個展遭到嚴厲批評,但她從未放棄自己的理念。她曾說:「這個世界充滿限制,但我想保有內在的自由。創作時,我想自由自在地去做,不在意他人怎麼想。」
即使到了百歲高齡,篠田桃紅依然持續創作。她的畫作清澈、靜謐,彷彿正映照著她的生活哲學。她的作品邀請我們進入一個寧靜的時刻,在筆觸、呼吸與沉默之間,專注地感受當下。
喬治亞·歐姬芙 Georgia O'Keeffe|看見世界的新方式
喬治亞·歐姬芙(Georgia O’Keeffe) 是 20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美國藝術家之一。她常被譽為「美國現代主義之母」,她的作品深植於美國西南的自然景色,卻傳達出跨越文化與時間的普遍感受。
歐姬芙於 1887 年出生於威斯康辛州,接受傳統繪畫訓練,但很快便覺得寫實風格過於受限。她不滿足於再現眼前所見,而是希望描繪內心所感。她的創作目標,是傳達一種情感上的對應,而非單純的視覺紀錄。
她相信,透過放大日常物件——無論是一朵花或一根白骨——可以打破我們對習以為常的視覺慣性,進而開啟新的觀看方式。她的畫作並不在於單純描繪自然,而是靜靜探索形式、空間與感官知覺之間的細微關係。
歐姬芙在城市與自然之間來回穿梭。在紐約,她描繪摩天大樓與都市景觀;但真正改變她藝術軌跡的,是美國西南部的沙漠地景。1930 年代,她開始在新墨西哥州生活,並最終遷居當地。那裡的白骨、岩壁與無盡天空,成為她創作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。
她的藝術外表看似強烈鮮明,實則內斂深沉。歐姬芙邀請我們放慢腳步、用心觀看、感受當下。她的作品就像一封無聲的邀請信,即使視線離開,餘韻仍長久停留在心中。
© Dans Le Gris 版權所有。未經許可,不得複製或轉載。
閱讀更多藝術文章:
• 現代藝術必知的 8 大流派——從印象派到超現實主義
• 當代藝術的影響力——它如何改變我們的現代世界?
• Fluxus 激浪派藝術運動:藝術是我的生活,我的生活就是藝術
• 包浩斯風格與代表人物:影響現代藝術與設計的先驅
關於我們
Dans Le Gris 源自於 Wassily Kandinsky 的作品,同時也是法語「在灰色」的意思。就如灰色所傳遞的氛圍,我們希望以純粹、極簡和永恆的設計來豐富日常生活。
在我們的線上刊物中,我們不定期地分享有關藝術、文化和設計等文章。我們精心挑選的內容包含了生活的多個方面的主題,希望能提供你有價值的觀點和靈感。謝謝你的閱讀,希望你喜歡我們的內容。